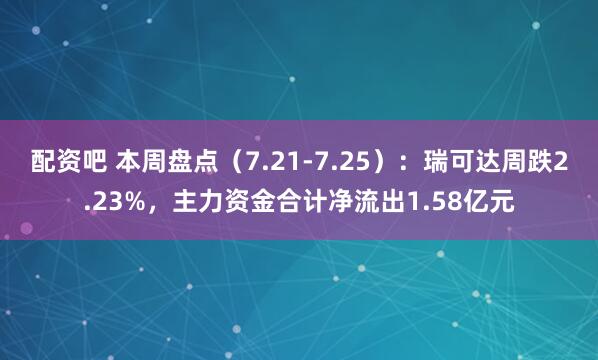文|星海配资吧
编辑|星海
文|星海
编辑|星海
《——【·前言·】——》
他第一次登基掌控契丹,第二次登基成为大辽皇帝,中原政权在他脚下覆灭。
他统治疆域锐变,军事威势高涨,却在死后被剖腹腌制,汉人称作“帝羓”——这个枭雄的一生,阴影与光环交织。
权势积累与第一次称帝之路
耶律德光生于契丹贵族家庭,其父为耶律阿保机,母为述律平。儿时陪同父亲征战,掌握骑射与部族治理技巧。他年轻之时就被委以重任,参与对渤海、回鹘、吐谷浑等周边政权的军事行动。
展开剩余89%战功多次累积,声望在契丹贵族中迅速提升。922年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开始负担起全契丹的军事指挥与边疆防卫重任。
契丹尚处部族联盟阶段,耶律德光的崛起,正值契丹社会从部族鬆散向中央集权与军事行政并重的转型期。
父亲耶律阿保机透过征战与兼并增强契丹对周边的控制,而耶律德光肩负实战任务,多次领军出塞。他随太祖灭渤海国,攻陷渤海都城忽汗城,作为前锋战将参与那些行动。他的军事才干与统帅能力,由此初现端倪。
926年,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天显元年七月二十七日病逝。述律平摄政,太子耶律倍虽为嫡长子,却被排在权力之外。耶律德光乘势掌实权。权力集中于他,部族诸将、官吏多数效忠于他的军事权限与行政能力。
政令开始以他为中心下达,朝廷大事由他拍板。契丹贵族有部分反对嫡系继承,但权力结构已经倾斜。
927年12月11日,耶律德光正式即位为契丹皇帝。这次即位标志第一次登基。他改制行政机构,加强律法制定与钱铁制度建设。他铸“天显通宝”等货币,与汉地铸钱制度参照,引入汉人书吏管理契丹南部汉人居住区。
设南北两面官制度:在汉人居住区域施汉制治理,在本部维持契丹部族传统方式。燕云十六州在此后被纳入契丹版图前期管理,成为对中原外交与军事准备的重要基地。
帝号初期,耶律德光治理契丹之内务稳定。任命宰相韩知古守尚书左仆射、中书令等重臣。设中书门下、南府北府诸宰辅,以汉人为政事使、平章事等职,调汉人与契丹贵族共治。官僚体系与财政赋税制度逐步形成,契丹的治国结构由父辈的部族联盟式军事首领进一步制度化。契丹越来越显露出帝国前期的面貌。
中原战争与第二次帝号确立
中原五代十国局势混乱。后唐内乱严重。石敬瑭作为河东节度使,对后唐朝廷不满。他向契丹求援,条件是割让燕云十六州。耶律德光在936年出兵南下,会同石敬瑭联合作战。在晋阳下击败后唐军队。战役胜利后,石敬瑭被册立为后晋皇帝,后唐灭亡。
契丹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后,将幽州改称南京,云州改西京,以作为统治中原北部的军事与外交前哨。那一区域成为契丹向南发展的跳板,契丹军队与契丹管理官员逐渐介入中原事务。耶律德光对中原事务施加影响,并实行南北面官制度管理汉人地区。
后晋成立后,初期对契丹采取臣属关系,但随着时间迁移,矛盾逐渐显露。后晋统治力量在中原疲弱,内政腐败加重。947年初,耶律德光再度南征。军队跨越黄河,攻入东京(汴梁)。后晋皇帝石重贵无力抵抗,被迫接受契丹控制。契丹军进入东京城中,掌握宫廷与朝政仪式。
947年2月24日,他在东京下诏改国号为“大辽”,改年号为“大同”。自此正式称辽朝皇帝。第二次登基标志辽朝取代五代政权在中原的一部分权力。向南面进驻后,中原礼仪被部分接纳,他在东京接受百官朝贺仪式,设南面官以管理汉人事务。
南征期间政策连发征粮制度引起民怨。中原地区粮食、布帛、牲畜等物资被征发。耶律德光在东京设置官吏,管理当地事物,但汉地百姓对契丹官吏与他们进行的征调与赋税感到负担重。北京(契丹的南京)与中原间补给线长、运输困难,许多资源由边境地区运入,中间遭遇盗匪与交通问题。
耶律德光称帝后不久,察觉南征常驻中原之难。他在大同元年正月进入东京接受礼仪,又因物资掠夺政策引发中原民众反抗。因局势不稳,他决定北返。从东京离开后的行军中,士卒疲惫,夏季酷暑与疾病并行。北返途中病情加剧,直至栾城之地逝世。
病重北返与死亡过程
大同元年四月,耶律德光自东京北返。南征后晋取得汴京,国号改辽,但短暂安定并未维持太久。他一路西北折返,兵马行军艰难,酷暑侵袭,环境酷热,军中多病。史书中称其“至临城得疾”,行至栾城“病甚”。腹中热症交错,手足胸腹热疼,时人以冰块冷敷胸腹手足,并饮冰以缓症状。
他病至栾城县杀虎林一带,病情进一步恶化。那里的气候与地形,加之北返途中物资运输难度极大,粮草、饮水补给跟不上。随行医师与近侍见状,多次劝他停留调养。一日夜间,他侧卧营帐,寒热交替,呼吸急促。史书中称他“苦热”。行军队伍被迫停下。帐中布置简陋,随从照料。医药以草药与冷敷为主,无力根治重症。
死亡来得迅速。病未能复原,一夕之间病势加剧。四月廿二日,在栾城县杀虎林之地逝世。记录中标明死亡当日天气炎热,身体饱受劳苦,寒热交替频繁。他未能回到北方本部。
死讯传出,当场随军人士进行遗体处理。契丹人依照本族习俗,考虑尸体返葬途中易腐败,决定对遗体采取防腐保存措施。随行人员打开其腹腔,取出肠胃,以盐填实。使用盐量巨大,史书称“实盐数斗”,将内脏掏去后,以盐沃之(即盐涂或盐填充)用于防腐。
处理完毕后,遗体与被腌制之部位装载于车驾或驮马之上,沿原路北返。队伍缓行,带着这具经过盐腌的遗体穿越河北境内。汉地史书中描述当地人对这具“帝羓”的称呼由来,即汉人见此腌制之尸称为“帝羓”,意为皇帝的肉干。传闻中“帝羓”成为日后民间与史书对耶律德光遗体处理方式最常用的标记。
北返途中天气依旧高温。盐腌虽然能减缓腐败,但遗体仍散发腥臭。行进艰难,车辆颠簸,随行车马因雨露、泥泞与颠簸频发,人员疲惫。车队中有负责守护尸体的护卫与医药随从,不断换敷冷湿布,调整体位,以保持尸体完整。
抵达契丹首都(或上京)后葬于怀陵。怀陵为耶律德光陵寝之所在。陵墓建于北地山川间,有祭殿、有守陵官。有史书记载葬礼庄重:辽朝贵族、宗室、汉地官吏均参与。其庙号“太宗”,谥号“孝武睿文皇帝”。陵地选在稍偏僻处,以草原山川为屏障,陵园规模与配套设施比照契丹帝陵例制。
史书记载变体较少:史官对于“病甚”“实盐”“剖腹”“载北去”“帝羓”之说一致。例如《资治通鉴》、《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皆有“契丹人破其尸,摘去肠胃,以盐沃之,载而北去,汉人谓之‘帝羓’”的记载。
史书记载变体较少:史官对于“病甚”“实盐”“剖腹”“载北去”“帝羓”之说一致。例如《资治通鉴》、《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皆有“契丹人破其尸,摘去肠胃,以盐沃之,载而北去,汉人谓之‘帝羓’”的记载。
遗体腌制与北返的整个过程耗时数日。军中医药人、护卫与仪仗官共同参与。遗体处理完毕后,北返路线经河北边境地区,州县有人目击车队。汉地地方官员在记录中提及沿途见闻:百姓或关门闭户,或远观而避,不敢近视,惧于陛下尸体之气与仪仗之盛。
耶律德光死后南征留下的空档,使契丹政权内部对继承问题立刻浮现。宗室与将领在他死后围绕帝位立谁为继承者开始讨论。这些讨论与他死亡与遗体处理并行,被史书简略记载为“国家无人君,宗室将领困惑”。但主线仍为遗体处理,即“腌制”“帝羓”“北归”等。
“帝羓”典故与遗体处理方式
耶律德光死后,契丹人对其遗体实施了一套在史籍中多有记载的处理方式。这种方式在汉地史书中称其遗体被做成“帝羓”。“羓”字原意为游牧民族用盐腌制牛羊肉储存食物之意。
多部史书有“契丹人破其腹,摘去肠胃,以盐沃之,载而北去,晋人谓之‘帝羓’焉”的记载。史书版块如《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资治通鉴》都有此记载。典籍中提及“载运而去”“汉人目之为‘帝羓’”表明汉地史书作者对这一做法感到震动或异样。
多部史书有“契丹人破其腹,摘去肠胃,以盐沃之,载而北去,晋人谓之‘帝羓’焉”的记载。史书版块如《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资治通鉴》都有此记载。典籍中提及“载运而去”“汉人目之为‘帝羓’”表明汉地史书作者对这一做法感到震动或异样。
遗体最终被葬于怀陵。怀陵为辽太宗之陵,位于怀州城北约六公里处。陵墓在地形中有内外陵区,设祭殿。怀陵为后续辽穆宗也被安葬之地。
陵园建设包括陵墓本身、祭殿、城墙、石柱等设施。考古资料表明怀陵遗址存有祭殿遗址、石墙、墓道面砖瓦散落等遗迹。史书并未明确提到腌制后遗体在陵墓中展示或作为木乃伊形式长期保存。
“帝羓”称呼流传于汉地人中,用以指辽太宗死后这种遗体处理方式。书面记录指此法为契丹异俗。并无史书证明人们将腌制后的遗体视为肉干食品或食用,仅为保存尸体之用。契丹风俗中,对高贵人物葬礼与遗体处理有传统方式与特例,耶律德光的遗体处理被记录为此类特例。
怀陵的陵园建设在死后由辽朝政权动员劳力修筑。尸体归葬怀陵后,政府举行葬礼,参与者有契丹贵族、汉地官吏、军事将领等。遗体未被公开展示,陵墓中多设祭殿供祭祀。陵园位置山势高,三面环山配资吧,且有水源溪流环绕,环境隐蔽。
发布于:北京市五五策略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